挖机的那些事(107)生活历尽波折,父亲生病住院
 东风日铲
2024-01-02
东风日铲
2024-01-02
8333
20
这一夜我又是辗转难眠。隔壁房间住进来一对男女,凌晨两点还不消停,床板撞在墙壁上扑通扑通扑地像拆迁似的。女人还叫得欢,越叫男人越卖力,身上似乎搭载了200匹马力的发动机,动力源源不断。我浑身燥热难耐,上了顶楼天台吹了一夜凉风。直到东方泛起一丝红霞,我才打着呵欠回了房间。
这一觉睡到傍晚,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出去找吃的。钱福来对我喊的话,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。即便是早上我能醒来,也不可能去国道口和钱福来会合。我在天台上抽了一整包烟,思来想去始终都坚持自己的原则。本本分分做人,踏踏实实做事,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。小时候偷了邻居张寡妇家腊鱼,父亲拿竹条抽得我直跳脚。他的话我记忆犹新:穷要穷得硬气,不偷不抢,挺起胸膛做人。钱福来错了,虽然我父亲老实一辈子,没给我创造什么财富,可他教我做人的道理,对我的教诲却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道不同不相为谋。我以为从此钱福来会和我分道扬镳,想不到没过几天,他让胡子来旅馆给我带话:你那个姓雷的朋友,让福哥给你捎句话,你家里出事了,赶快回去……
我来不及多想,旅馆刚交的几天房费也不要了,开着车子就往家赶去。上了国道,手机开机后我就拨打父亲的电话。电话没人接,还好母亲的电话在等待几秒钟后终于被接通了,母亲的声音嘶哑而无力,她说我父亲住院了,昏迷两天都没醒,现在在县人民医院。
县人民医院门前那条路很窄,而老式医院没有地下停车位,车位严重不足。进医院的车辆都是出一辆进一辆,因此这条路上长年拥堵不堪。离医院还有两个红绿灯的距离,我就把车拐进一家商场的停车场,然后一股作气跑到了医院。
找到父亲的病房,母亲趴在父亲床头打着盹。听见脚步声,她立刻惊醒过来。抬头一见我顷刻之间眼眶湿润了:洋洋,这些天你哪去了,家里可不能没有你。
我心里五味杂陈不是滋味,看着父亲躺着病床上,眼睛都不眨一下,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惶恐涌上心头。
母亲见旁边床位的病人在闭目养神,只好示意我到外面说话。走廊尽头有一间房,是一个椭圆形的落地窗式观景台。母亲刚走进观景台,忍不住泪眼婆娑。她向我倾诉起父亲病倒的缘由,全都是姚顺那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害的。我不在家这些天,三一215的分期D款忘了还。仅仅逾期三天,姚顺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,电话打不通就找到我家里。我父亲拿不出钱来,姚顺就冷嘲热讽说些难听的话,污蔑我和高富帅同流合污,分了脏款就玩失踪……我的父亲气得浑身发抖,难以置信眼前这个面目狰狞的人,就是当初为了怂恿我买挖机,提着礼品上我家把他二老当菩萨一样贡起来的笑面虎。
看清姚顺的真面貌后,父亲也不跟姚顺客气了,铁着脸下了逐客令。姚顺走后不久,父亲身子一软就晕倒在地。母亲慌了,也不会拨打急救电话,只得跌跌撞撞一路小跑,到二叔家找二叔帮忙。二叔开着他那辆拉水泥的三蹦子,拉着二老两人,送到了县人民医院。
我紧握的拳头颤颤发抖,恨不得将姚顺大缷八块。母亲低声吟泣了一会,又说,对了,医生叫我签了个通知单什么的,我也不识字,只听见医生说你爸的病情很危险……
我找到主治医生,医生确认了我的身份,拿出一张签着母亲名字的病危通知书,说,你怎么现在才来?你爸是脑卒中,医学上也叫脑梗,俗称中风。病情危急,赶快把病人转到市医院去……
父亲上一回住院,也是脑梗。只不过及时送医,打了两天吊瓶就恢复了。想不到这一次复发这么严重,此时医生在我面前,比如来佛祖还要法力无边。能救父亲的除了他们,没有别人了。我的语气虔诚到卑微的地步:医生,市内哪家医院比较好?
市中心医院,可以报合作医疗的。条件允许的话,最好是同济,协和……快去办转院手续吧,不能再等了。
我如同接到圣旨一般,回父亲的病房匆忙通知母亲收拾衣物,就去办理转院手续。救护车绕上了去往省城的快速通道,天刚擦黑。经过一个小时的煎熬行程,我在市区高架桥上,远远年到协和医院四个通红的大字时,父亲的手指微微颤抖了一下。我激动不已,相信父亲一定会醒过来,一定能够康复回家的。
大医院的效率就是高。救护车停在急救中心门口,我还没下车,几个医护人员就作好了抢救的准备工作。一名留着学生短发的女医生,看了县医院的病历报告单后,马上安排医护人员把我的父亲推进ICU病房。我甚至连登记都没录完,就早早看不到父亲的人影了。
ICU是重症监护室,医院规定不允许家属陪同的。我和母亲隔着玻璃门窗,只能模糊地看见父亲半张脸庞。回头看着母亲布满血丝的双眼,满脸的憔悴,我心疼不已。父母病倒了,母亲不能再倒下。我的车停在县人民医院,只能打车送母亲回家休息。然而任我怎么劝,母亲不肯离开半步。ICU病房不让进,她就睡走廊,睡楼梯。拗不过母亲的固执,我只好去租了一个床位,下楼买了被褥和简单的生活用品,将母亲安顿下来。
出了医院大门,我这才稍许缓口气。深夜城市街道上,依旧有不少来往的行人。他们脚步匆匆,面色冰冷。没有谁去关心谁的冷暖与否,更没有谁倾听谁的悲欢离合。这里的夜空很深邃,仰着脑袋才能看见稀稀落落的星光点,不像官桥,站在窗前略一抬头,星星离得很近,月亮似乎就在眼前。哪怕没有灯火,官桥的夜晚都是亮堂堂一片。抽完了一支烟,我挡下一辆出租车,往回家方向驶去。
我回家主要是给母亲带几件换洗的衣服,她的手机落在家里有事也不方便。从县人民医院取车到家,快凌晨两点了。楼上卧室的灯还亮着,这样我就放心了。母亲不在家,余丹丹还记得接儿子放学。若不是接送儿子,她能十天半个月呆在棋牌室和美容院不回家的。
儿子怕黑,床头一直开着他喜欢的卡通感应小夜灯。这灯是我买给他的,晚上自动开启,白天熄灭。淡蓝色的光下,儿子的嘴角在恬静的梦乡里,微微撅起甜甜的微笑。看着他安静的样子,我的内心也平静下来。年少轻狂的时候,喜欢追求大风大浪。然而当我累了,想找个避风港休息的时候,我才渐渐明白,生活最终的样子,不应该就是平平淡淡吗?就如同此时此刻,安安静静地守护自己的孩子,自己的家人。
推开卧室的门,来到自己的房间,心情瞬间坠落到冰谷。余丹丹斜躺在床上,沉睡中还戴着耳塞,手机在枕边还播着电视剧。床头床尾推着的杂乱的衣服,包包,快递纸盒,几乎将她包围。而这张床上,已无我的容身之处。床头柜旁的垃圾桶下,淌出一滩褐色的污渍,墙上还粘着几根风干的泡面。而我一个月之前从工地回来晾在窗台上的鞋子,淤泥也早已干成土块,零零碎碎地散落一地……儿子房间里的温馨的一幕,无法隔化我心底的寒冰。我拖着沉重的脚步下楼,收拾了几件衣物,启动车子头也不回地离家而去。
我在医院附近的宾馆开了一间房,和母亲轮流照看父亲。大医院的技术设备果然不一般,输了两天液后,父亲就清醒了过来。母亲喜极而泣,我也忍不住泪湿眼眶。看着父亲消瘦的脸,我难受得快要窒息。父亲第一句话是:饭熟了吗?
他还以为是在家里,肚子肯定是饿了。我给他喂稀饭,轻轻地吹着热气,就如同他年轻的时候,哄着年幼的我吃饭一样。时光的轮回如此之快,岁月的脚步那样匆忙,我甚至还来不及回味年幼的童贞,年少的轻狂,蓦然回首,那些回忆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。而此时的父亲,也不再是年轻时骑着自行车,载着我一路风驰电掣自壮年男人。他像一个在黑暗燃烧的烛火,虚弱得经不起一丝风寒。
父亲挺过了一个星期的危险期,病情逐渐平稳下来。他能够开口说话,手脚做一些轻微的动作,我和母亲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。我以为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,但是面对厚厚的一叠催费单,我还是辗转难眠,思绪万千。
我身上确实拿不出钱了,几张银行卡凑起来,也就两千多块钱。对于十几万的住院费,无异于杯水车薪。三一215挖机被公司锁机了,金融公司的还款日渐渐迫近。身边的人,除了黄飞,没有一个能够开口的人。张全真买了房,装修款欠人家的没给。雷洪波这几年挣的钱,刚刚还完小松挖机的借款,利息都付了十多万,指望他也难。看来,只有把希望寄托在黄飞身上了。
我把车开到加油站,生平第一次加了200块钱的油。以前都是豪横地把油加满,顺便搭讪一下加油站漂亮的妹子,这次却不好意思抬头看收银员。
我在官桥威斯特大酒店的客房找到了黄飞,他正和商砼站的老杜打牌。黄飞不知道什么时候,脖子上挂上了一条金项链。尽管房间里烟雾缭绕,金项链的光茫仍然十分亮眼。而他这条链子,和老杜手腕上那块劳力士手表比较起来,就显得相形见绌了。我脸上挤出生硬的笑容,挨个给他散了一圈烟。黄飞对于我的出现,并没有感到丝豪意外,油库的事也绝口不提,仿佛压根没发生过一样。
等了好一会,好不容易趁老杜接电话的机会,我把黄飞拉出了房间。走廊里很安静,只是隐隐听到楼下KTV传来客人唱歌的声音。
什么事在里面说不行吗?
黄飞的表情依旧是那么平静,但我却再无力掩饰内心的焦虑,开门见山就道明了来意:飞哥,我爸爸住院了,重症监护室躺了十多天。这回只有你能帮我了……
黄飞“哦”了一声,双手抱胸靠着墙,问:怎么会这样?
都是姚顺那个王八蛋害的……忽悠我买挖机的时候,甜言蜜语信誓旦旦;现在资周转不开,才逾期几天没还D款,他变得比黄世仁还狠。我爸就是被他逼进医院的……
我气得咬牙切齿,恨不能走到窗前对着官桥街把姚顺祖上十八代痛骂一遍。黄飞指了指房门,做了个轻声的动作。隔墙有耳,屋子里都是和姚顺关系熟的几个人,可我不在乎。黄飞见我怒火难平,只好安抚我说:你发个账号我,我先凑5000块给你。我手上也只有这么多了……
那不够啊飞哥……我几乎哭丧着脸,语气也颤抖起来: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,一天就得一万多啊。我不是找你借钱的,上回油库没钱进油,不是我垫的款吗?你把我那十万给我,后面挣的钱我一分不要……
黄飞眼珠一瞪,嗤嗤笑起来:你没搞错吧,油库都黄了,物资全都被没收了,我上哪给你弄这么多钱去?
我早就知道黄飞会拿油库查封这事当借口,也只得退而求其次,语气缓和下来,道,飞哥,油库没了,账还在啊。我不要十万了,我替你垫的那一半给我可以吧。我只要五万,那可是我私下借你的,你当时不是说过几天还给我吗?
我以为提起私交,以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,以我对他的信任,他是不可能不认账的。但是我的想法太单纯了,黄飞并有半点退让的余地。他掏出手机,翻出几张图片,什么罚款单,酒水消费单,让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看到了吧,油库的罚款,疏通关系都是我去处理的。你自己手机一关,两耳不闻,得了便宜还卖乖。要不是我渠道灵活,我早被关进去吃皇粮了……
是我先关的手机,是我先跑的路?我冷笑着,目光直视着黄飞。这么多年来,无论我吃多少亏,从来都忍气吞声,对他心存敬畏。虽然年龄相仿,毕竟他是我的师傅。平时请客吃饭我买单,逢年过节赶情送礼,甚至他在我面前趾高气扬地吆五喝六我也言听计从。我不在乎在他面前扮演小丑的角色,我只在乎自己的原则,黄雀衔环不忘初心。然而我的感恩之心,换来的却是黄飞的置若罔闻,冷漠无情。
我仍然不想放弃最后一丝希望,可不等我开口,房门开了,探出一个脑袋,冲黄飞喊起来:搞什么飞机,牌还玩不?
黄飞双手插兜,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门关上的那一刹那,我终于清醒地认识到,我和他从始至终都不是一路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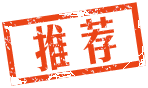
 维修挖机666
2024-04-14
维修挖机666
2024-04-14
 挖机智多星288
2024-04-03
挖机智多星288
2024-04-03
 挖机界吴彦祖
2024-01-21
挖机界吴彦祖
2024-01-21
 挖机小温侯832
2024-01-18
挖机小温侯832
2024-01-18
 老五183****5513
2024-01-13
老五183****5513
2024-01-13
 挖机赤练仙子1335
2024-01-13
挖机赤练仙子1335
2024-01-13
 挖机赤练仙子1335
2024-01-13
挖机赤练仙子1335
2024-01-13
 太阳港
2024-01-13
太阳港
2024-01-13
 w1026592003
2024-01-11
w1026592003
2024-01-11
 凡尘666
2024-01-05
凡尘666
2024-01-05





